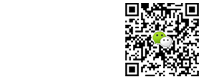机房防雷接地工程设计方案
污染摄入型违规是运动员通过一定污染源或中介体被动摄入禁用物质导致阳性检测结果,可分为产品污染型、肉类污染型、密切接触型、其他污染型和来源不明型5种类型。通过对国际体育仲裁院近10年相关裁决的实证分析,归纳出实然层面认定影响禁赛期减免的因素及其逻辑联系,并与《世界反条例》的应然要求相对照,形成包括“禁赛期认定逻辑流程图”“非故意检视对照清单”和“过错程度评估对照清单”在内的禁赛期减免模型。该模型不仅有利于国际体育仲裁院和世界反机构提高工作效率与质量,更加有助于运动员事前增强污染摄入防范意识、事后积极争取禁赛期减免,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随着社会环境日益复杂和化学添加剂滥用情况的增多,因污染途径摄入禁用物质导致运动员违规(anti-doping rule violations,ADRV)的案件时有发生。在此类仲裁案件中,运动员通常会提出免除或减少禁赛期的请求,但最终能获得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CAS)支持的情况却并不多。在实体争议性质的禁赛期减免因素方面,国内现有研究大多分布在在“非故意”(李智 等,2023;王倩倩,2019;周青山 等,2022)、“无过错或无重大过错”(郭树理 等, 2021;宋彬龄,2012;虞志波 等,2021)、“人格证据”(章语馨,2022)等方面,鲜有系统研究禁赛期减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成果。相关实证分析往往基于少数经典案例,鲜有基于大量CAS案例进行的实证研究。
其实,涉案运动员的核心关切通常是减轻处罚,特别是减免禁赛期。面对反机构的组织优势和专业背景,处于弱势地位的运动员不仅在实践中难以获得禁赛期减免,在理论上也几乎没办法得到现有学术成果的直接指导。污染摄入型案件本就具有意外性,不幸涉案的运动员往往不知所措,也不了解如何最大限度减轻案件给我们自己所带来的损失和影响。
因此,本文旨在结合《世界反条例》(World Anti-Doping Code,WADC)的相关规定,通过对CAS近10年相关裁决的实证研究,归纳出污染摄入型违规案件中所有可减免禁赛期的实体争议性因素及其逻辑关系,在严格遵守管理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厘清运动员主张禁赛期减免的可行理由和相关主张。达到充分了解禁赛期减免逻辑、合理评估预判禁赛期、迅速开展证据收集、保护运动员合法权益之目的。
事实上,WADC还有关于“立功”“和解”等程序性禁赛期减免因素的相关规定,但本文并不涉及相关联的内容,只研究违规本身所涉实体争议的减免因素问题。
本文以污染摄入型违规案件为研究对象,在实体争议层面探究认定和减免运动员禁赛期的因素。对于这类案件,有学者将运动员因摄食食品或药品导致阳性检测结果的违规案件称为“食源性违规案件”(郭树理 等,2021)。原因是在食品安全领域,早有关于食源性污染的研究,故沿用了这一提法。但这一界定类型下的案件并非在法律适用、证明标准、构成要件等方面具有一致性或相似性,只是在行为方式上类似。因此,本文选取可能涉及污染内容的足量样本,在剔除非摄入型案件后,结合样本共性与特性,对此类案件进行界定和分类。
裁决书是CAS在仲裁过程中就案件实体和程序问题制作的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的正式文书,是CAS裁决思路和态度的重要载体,能客观、直接反映污染摄入型违规案件全貌。
本文以CAS运营的CAS decisions数据库()为大多数来自,以学术研究型法律数据库DOPING.nl()为补充,最大限度保证样本数据的完整性。
基于上述两组数据库,以“contaminated”①为关键词,以2014年1月1日—2024年1月1日为时间段进行检索。在排除重复裁决和部分裁决后,初步筛选出162份裁决书。进一步排除非摄入型污染(如尿样被“污染”、赛马饲料被“污染”等)的69份裁决书、和解结案的4份裁决书、裁决结果不涉及运动员禁赛期的11份裁决书、仅引用“污染”相关案例但案情与污染无关的8份裁决书以及因超期不予受理的1份裁决书后,共得到69份裁决书。其中,3份裁决书涉及多名运动员②,将针对1名运动员的裁决视为1个案例,则本研究共纳入69份裁决书包含82个案例。
污染摄入型违规案件中的“污染”是指禁用物质通过某一污染源或中介体(产品、食物、人等)进入运动员体内的途径。初步分析样本案情发现,此类案件暗含非故意摄取禁用物质的主观因素(哪怕只是运动员宣称如此),运动员在被通知阳性检测结果后意识到自身的违规,均属于违反WADC第2.1条(存在禁用物质或其代谢物、标记物)的情形。结合“污染摄入”的文义理解和样本案情,可将污染摄入型违规案件定义为:运动员通过一定污染源或中介体被动摄入禁用物质,导致阳性检测结果的违规案件。
本文对样本中的禁用物质来源进行逐一整理分析,发现共有5种导致违规的途径:产品污染、肉类污染、密切接触、其他污染和不明来源。各类违规案件获得禁赛期减免的总体情况和趋势如图1所示。
在贾姆尼基案中,CAS指出“禁用物质可能被无意摄入运动员体内的3种途径”分别是“密切接触”“产品污染”和“肉类污染”③(CAS 2019/A/6443&6593)。而通过被污染自来水或非肉类食品等摄入禁用物质的情形(如CAS 2013/A/3370, CAS 2019/A/6541,CAS 2018/A/5592),无法纳入上述类别。再加上无法确定来源的情形,可以将污染摄入型违规案件分为5种类型:产品污染型、肉类污染型、密切接触型、其他污染型和来源不明型。
③虽然肉类也是一种“产品”,某些密切接触型兴奋违规剂也是源于密切接触对象使用了含禁用物质的“产品”,但CAS显然区分对待这3种途径,相应的禁赛期减免结果也存在比较大差异。
产品污染型是指运动员因使用含有禁用物质但标签中未注明或通过适当网络搜索未发现该信息的产品而导致的违规。这种形式是早期污染摄入型案件的主流,并跟着时间推移慢慢地减少(图1)。样本案例中有47个为产品污染型,占样本总数的57.3%,其中仅5例通过CAS裁决获得禁赛期减免,且没有运动员获得免除全部禁赛期的裁决结果(表1)。这是因为服用营养品或药物等产品之行为本身就存在极高的违规风险。世界反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WADA)始终致力于相关宣传教育,进一步提升了运动员在此类案件中的注意义务,使其难以通过无过错(no fault or negligence,NFN)或无重大过错/疏忽(no significant fault or negligence,NSF)寻求禁赛期减免④。
④WADC(2021) 10.6.1.2 的释义指出,运动员服用营养品的风险自负。除非运动员在服用受污染产品前已经高度谨慎,否则以NSF为由减轻处罚的做法很少适用于此类案件。
肉类污染型是指运动员因食用被禁用物质污染的肉类而导致的违规。随着全球养殖产业化发展和肉类进出口普及,该问题于2015年前后出现,并于2019年后慢慢地发展成为当今污染摄入型违规的主要形式之一(图1)。此类案件中,相关禁用物质一般是畜类饲养添加剂,有些在畜类供应地极普遍甚至是合法的。样本案例中有11个为肉类污染型,占样本总数的13.4%,其中通过CAS裁决获得禁赛期减免的有3例,且运动员均获得了免除全部禁赛期的裁决结果(表1)。与产品污染型违规相比,肉类污染案件中运动员的注意义务及禁用物质来源证明标准相对更低,获得禁赛期减免的概率也大得多。
密切接触型是指运动员因与他人或他人使用过的物品密切接触导致摄入禁用物质的违规。此类案件常发生在家庭或情侣生活的私人场合,运动员通过亲吻、饮食、接触和共用物品等行为无意中摄入禁用物质。样本案例中有5个为密切接触型,占样本总数的6.1%,其中通过CAS裁决获得禁赛期减免的有2例(表1)。样本案例显示,只有在任何理性人看来都足够安全私密的环境,才可能降低运动员的注意义务。例如,CAS 2017/A/5296案发生在情侣生活场合,CAS 2019/A/6482案发生在直系亲属家庭聚会场合。满足此种环境前提,运动员很有可能获得免除全部禁赛期的裁决结果。
其他污染型是指除产品污染、肉类污染和密切接触途径以外,运动员通过被污染的环境或中介物摄入禁用物质的违规。样本中该类案例仅有3个,占样本总数的3.7%,其中通过CAS裁决获得禁赛期减免的仅有1例(表1)。虽然此类污染途径极为罕见,也只有在极特殊情况下才可以获得CAS的认可,但不可以忽视其出现的可能,且不能排除未来出现无法纳入前述类别的新型污染途径,故有必要将这一类型单列出来。
来源不明型是指运动员不能确定禁用物质来源或无法将其主张的来源证明到优势证明标准以上,但存在未经证实的污染来源导致违规的情况。WADC(2015年版)生效前,此类案件没获得禁赛期减免的先例,是因为WADC(2009年版)规定的禁赛期减免路径均以证明禁用物质来源为必要条件。WADC(2015年版)生效后,即使无法证明来源,运动员仍可能通过证明“非故意”将禁赛期从48个月缩短至24个月。样本案例中有15个为来源不明型,占样本总数的18.3%,其中通过CAS裁决获得禁赛期减免的仅为3例(表1),且均未获得免除全部禁赛期的裁决结果。
实证研究中的文献研究方法是用科学方法收集和分析文献资料,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历史考察与分析的方法,一般来说包括文献确定、选择分析文本、分类及编码、分析资料和效度检验4个步骤,通常还具有促进文献应用的研究目的(雷小政,2019)。本文主要是采用该研究方法中的定性分析法,按照以下步骤对污染摄入型违规案件中的禁赛期减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
第一步,确定文献及编码。以样本裁决书呈现的82个案例为研究文献,对文献进行编号,逐一翻译、整理。设计统计表,从案号、运动类型、裁决作出时间、上诉人、被上诉人、禁用物质类型、法律依据、禁用物质来源、故意情况、过错情况和最终禁赛期11个方面记录样本信息。
第二步,对考量因素进行类型化分析。归纳样本裁决书认定的禁赛期减免因素并进行层级分类,对每类减免因素所关联的案例分别进行正面和负面的列示,并分析其合法性与合理性。
第三步,归纳形成模型。通过上述分析,厘清禁赛期减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形成包括逻辑流程图、检视与评估清单及其负面清单在内的污染摄入型违规案件禁赛期减免模型。
第四步,对模型进行检视与应用。将样本带入模型做验证,确定模型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推进模型的应用。
本文的82个案例中只有14名运动员通过CAS裁决获得禁赛期减免,其中6例获得禁赛期免除。从裁决结果看,污染摄入型违规案件中的禁赛期减免率是17.1%,禁赛期免除率仅为7.3%,运动员通过CAS裁决获得禁赛期减免的难度极大。
几乎所有支持运动员禁赛期减免请求的样本裁决书都对运动员的“非故意”和“过错程度”进行了讨论,且在实体争议(merits)部分无一例外地分析了“禁用物质来源”(source,以下简称“来源”),其中也有35.7%的裁决书论及人格证据。下面从来源、“非故意”、过错程度和人格证据4个方面,结合样本整理结果,分析上述因素在减免禁赛期方面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污染摄入型违规案件的禁用物质来源,是区分不同污染类型的关键,也影响着各类案件中运动员的注意义务(表1)。本文82个案例全部对来源进行了讨论,但其中只有24.4%的运动员能达到优势证明标准。这一标准很严格,通常包括以下原则:1)运动员必须证明其假设比其他解释可能性更大,至少达到51%的发生概率(CAS 2007/A/1370 &1376,CAS 2011/A/2384&2386);2)运动员可提出别的可能来源,但证明某一来源为若干种情形中可能性最大者,或排除其他情形,均不足以达到证明标准,另一方则没有义务提出其他竞争性情形,也无相应举证责任(CAS 2019/A/6541,CAS 2012/A/2759);3)仅有否认、清白历史和努力查明来源的行为,不足以达到证明标准,运动员一定要提交实际证据,而不仅是猜测(CAS 2014/A/3820);4)运动员一定要使用确凿的证据(如科学或其他证据)证明来源可能会引起实际的阳性结果(CAS 2010/A/2277)。
值得注意的是,肉类污染型案件的来源证明标准与其他污染摄入型案件不同,运动员只要能证明来源是被污染的肉类,即使无法确定准确来源,仍可能寻求禁赛期减免。确定特定的肉块被视为“愚蠢的差事,且会对运动员施加无法达到的标准”(CAS 2019/A/6443&6593)。运动员可通过提供“具体、客观、有说服力的证据”来支持其污染物来源的解释,包括科学证据和专业相关知识、其他总体性证据(如当地多名运动员出现此类污染结果等),以及阳性检测结果的延迟等(CAS 2022/ADD/46)。
为列示CAS认定“故意”的典型情形,本文整理了所有支持运动员禁赛期减免请求样本中的“非故意”证明情况(表2)。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整理样本中对运动员“非故意”认定不予支持的情形,从来源、客观方面、主观方面归纳分析“非故意”认定的依据。
WADC(2015年版)、WADC(2021年版)未将来源规定为证明“非故意”的必要条件,但根据10.2.1.1条的释义⑤,在未证明来源的前提下认定“非故意”几乎是不可能的。“来源”是对禁用物质进入运动员体内途径的描述,若能证明这种途径是被动的“污染”,本身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非故意”的证成。但该释义中“几乎不可能”的措辞也从反面表明,存在未确定来源却成功证明“非故意”的可能性。若运动员无法达到优势证明标准,也并非全无意义,至少要证明禁用物质来自污染途径的可能性,这也是CAS灵活审查案件其他情况并认定运动员“非故意”的必要前提之一(CAS 2016/A/4676)。CAS 2016/A/4919案认为“最罕见情况”下,即使运动员无法确定禁用物来源,也能证明“非故意”;CAS 2016/A/4534案则运用比喻方法,提出运动员能通过“最狭窄通道” 的例外情况。但这一“通道”无疑是极难通过的。除反机构对“非故意”无争议的情形外,62个无法证明来源的案例中,CAS认定运动员“非故意”的仅3例(CAS 2020/A/7579&7580,CAS 2018/A/5695,CAS 2018/A/5580)。
⑤WADC(2021)10.2.1.1释义:“虽然在理论上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可以在不说明禁用物是如何进入自己体内的情况下证明其违规不是故意的,但在条款2.1的违规案件中,运动员在没有证实禁用物来源的情况下成功证明其行为是非故意,绝大多数都是不可能的。”
在这一问题上,Sato等(2017)认为,WADC措辞不清导致了CAS裁决的矛盾对立;Rigozzi等(2015)认为,来源固然是一个重要甚至关键的因素,但CAS可以灵活审查案件所有主、客观情况,并决定违规是否“非故意”。本文认为,原则上应当证明来源,但特殊情况下可以不证明或降低其证明标准,同时有必要明确规定例外情形,防止仲裁员滥用自由裁量权。
虽然“非故意”是一种主观心态,但客观方面能印证这种心态的事实,比主观方面的依据更有说服力。以下是有助于证明运动员“非故意”的客观事实。
1)科学证据的吻合。若有科学证据说明,样本中的禁用物质浓度与污染摄入的药代动力学相吻合,将有力证明运动员的“非故意”(CAS 2022/ADD/46)。反之,科学证据不吻合或缺失是影响“非故意”认定的主要的因素。清白记录等主观依据,无法改变基于实验室结果得出的结论(CAS 2016/A/4761)。同时,毛发检测的证明价值也有争议,因为其最多只能表明运动员未长期摄入禁用物质,而不能排除故意使用(CAS 2020/A/6978&7068)。
2)公开被污染产品使用情况。运动员在检查记录单上登记案涉产品(CAS 2014/A/3685),或主动将其上交官方机构(CAS 2014/A/3572)等公开其使用情况的做法,一般被认为与作弊心态不符。反之,运动员未在检查表中申报含禁用物质的产品,将破坏其关于产品污染导致违规的解释(2017/O/4978)。
3)运动员自身能力优秀。若运动员或其所在团体具有高水平竞技能力,而即将面对的对手较之不具有竞争力,或已进入不重要的赛程,则没有冒险服用的客观必要(CAS 2013/A/3435)。尤其是世界级运动员或有天赋的年轻运动员,更没必要因灾难性的冲动放弃光明前景(CAS 2020/A/7579&7580)。但仅有这个理由是不够的,因为赢得比赛并非一定是运动员使用禁用物质的唯一目的,还可能有其他原因。如,胜过队友以期在新合同谈判中提高谈判地位等(CAS 2017/A/5357)。此外,运动员坚称自己拥有适合所在运动领域的完美身材(CAS 2016/A/4377),也被认为与“非故意”的证明无关。
4)摄入禁用物质有害无益。若所摄禁用物质的低浓度无法提高运动能力、极易被检查出来(CAS 2014/A/3572)或不利于运动员的运动能力及健康(CAS 2018/A/5695),则摄入该禁用物质有害无益,相应的,理性运动员都不太可能为此冒险。此外,为避免阳性风险,运动员也极不可能在已知晓即将受检后故意摄入禁用物质(CAS 2018/A/5580)。反之,如果运动员摄入的禁用物质有利于伤病恢复,即使对其运动能力提升无益,也会被认定为一种可能的故意动机(CAS 2020/A/6978&7068)。
运动员的主观心态无疑与“非故意”认定紧密关联,WADC(2009年版)甚至以“目的并非作弊”为涉特定物质禁赛期减免的必要条件。但在现行WADC制度下,这类依据均无法作为认定“非故意”的决定性因素,须结合其他证据使用。
1)摄入禁用物质之目的并非作弊。WADC(2021年版)对“故意”的释义⑥表明其不只有作弊这1种动机,还可包括放任自己违规、滥用药物上瘾甚至蔑视WADC的心态,但作弊无疑是运动员摄入最重要的原因。若运动员能证明摄入禁用物质的目的并非作弊,而是为提升外貌形象(CAS 2018/A/5583)、治疗其他疾病(CAS 2016/A/4676)等,则有助于证明其“非故意”。反之,运动员服用旨在提高成绩和促进康复的产品(CAS 2017/A/5282),则会被认为无视明显存在的风险,在“非故意”认定上获得负面评价。
⑥10.2.3条规定:条款10.2使用的“故意”一词是指某些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已经构成违规,或明知该行为具有构成或导致违规的高风险,但仍明显无视该风险而实施的行为。
2)真诚的外在表现和否认。运动员仅通过否认和解释不足以证明“非故意”,但并不代表真诚的外在表现和否认无益于证明。运动员对运动规则有成熟的认识,被认为是无必要因服用危及自己职业生涯的依据(CAS 2020/A/7579&7580);而坚称完全不知道营养品含禁用物质,也有助于证明无作弊意图(CAS 2014/A/3685)。反之,运动员具备有关的丰富知识,却谎称自己不了解相关风险,会被认定是作弊心态的体现(CAS 2019/A/6283)。
3)清白的人格和积极努力配合的举止。样本中以人格证据论证“非故意”的裁决均指出,人格证据绝非决定性因素。但违规发生前,运动员一贯的清白记录(CAS 2018/A/5695)、证言的可信度(CAS 2016/A/4676)、对待反教育的态度(CAS 2022/ADD/46),尤其在得到俱乐部经理、教练、队医等人的支持时,能超越单纯的否认(CAS 2019/A/6313);违规发生后,运动员在陈述和举证期间配合的举止、努力调查来源的积极举动(CAS 2018/A/5695)以及主动进行测谎和毛发检测等行为(CAS 2019/A/6313)都能作为证明“非故意”的依据。反之,如果运动员被证实说谎、捏造证据,或在仲裁过程中不合理地变更证言和证据(CAS 2016/A/4439),其可信度将受到负面评价。此外,运动员本人未出席听证程序作证(即使经济确有困难),也会被认为没有努力争取申辩机会,因为还有别的廉价或免费方法(CAS 2016/A/4377)。
在样本案例中,用以证明运动员“非故意”的依据还包括:年龄小、缺乏反教育(CAS 2018/A/5583)、污染产品没有可疑之处(CAS 2018/A/5580)、运动员无法预见污染可能性(CAS 2017/A/5296)等。不过,本文认为上述事实主要影响运动员的注意义务,应当是评估过错程度的考量因素。此外,反机构认可运动员“非故意”的,CAS可以直接认定运动员“非故意”(CAS 2019/A/6443&6593,CAS 2019/A/6482等)。
WADC中的NFN和NSF是两项分别用以免除和缩减禁赛期的独立理由,但在样本裁决书中,CAS往往不将它们分开讨论,而是通过列举影响过错程度的各项因素,综合分析得出运动员NFN或NSF的结论。如CAS 2018/A/5580案的裁决指出:“为确定NFN或NSF是否适用,仲裁庭一定要考虑该违规的所有相关情况,以评估运动员尽到注意义务的程度。”本文按照CAS裁决的常见思路,将两者作为一个体系讨论。
过错程度认定标准的建立可追溯到经典的西利科案(CAS 2013/A/3327&3335)。CAS在该案中指出确定禁赛期的决定性标准是过错,而评估过错程度须同时考虑客观和主观因素。该案基于WADC(2009年版)将运动员过错程度划分为“严重过错”(禁赛期16~24个月,通常为20个月)、“一般过错”(禁赛期8~16个月,通常为12个月)和“轻度过错”(禁赛期0~8个月,通常为4个月)。后CAS在艾拉尼案(CAS 2017/A/5301&5302)中基于WADC(2015年版)将过错程度划分调整为“一般过错”(禁赛期12~24个月,通常为18个月)和“轻度过错”(禁赛期0~12个月,通常为6个月)。
为列示CAS认定过错程度的典型情形,将所有支持运动员禁赛期减免请求样本中的过错程度认定情况整理如表3所示,并比照西利科案和艾拉尼案中的认定标准确定过错程度。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整理样本中对运动员过错程度的认定情况,从来源、客观方面、主观方面归纳分析影响过错程度评估的依据。
在现行WADC制度下,无法证明来源也可能基于“非故意”获得禁赛期减免,但来源证明仍被作为基于过错程度减免禁赛期的前置条件(受保护人员和大众运动员除外)。即使已被认定为“非故意”(禁赛期减至24个月),若无法证明来源,受保护人员和大众运动员之外的普通运动员也将无法基于NFN和NSF获得进一步的禁赛期减免(表1)。
结合西利科案(CAS 2013/A/3327&3335)对客观标准的要求,认定过错程度应考虑两点:一是运动员尽到谨慎注意义务的程度,即评估运动员采取一定的措施以避免违规的情况;二是运动员对合理期待的达成程度,要求结合具体案情去分析一个理性运动员在当时情况下对其应有期待的满足程度(郭树理 等,2021)。本文从这两方面出发,整理了样本中基于过错程度减免禁赛期的客观依据(前3项为运动员积极履行注意义务的因素,后2项为客观上减轻运动员注意义务的因素)。
1)对使用产品做研究和检索。针对产品污染型违规案件,CAS反复强调,履行最大限度注意义务的基础要求是检查产品标签与进行网络搜索(WADC Commentary Team,2017),这是运动员应履行的基本义务,包括但不限于认真查看所用产品(特别是营养品)的包装和标签(CAS 2016/A/4676)、充分进行互联网检索和研究(CAS 2013/A/3435)以及比较产品成分清单与禁用清单(CAS 2018/A/5580)等方式。反之,不履行该义务很可能被认为“过错程度严重或相当严重”,即使在“非故意”的前提下,也可能被裁定禁赛24个月(CAS 2016/A/4676)。即使是未成年运动员,不亲自履行该项义务也会被认定为“应发挥更非消极作用”(CAS 2018/A/5580),没有办法获得较大程度的禁赛期减免。
2)产品经过专业技术人员/机构认可。运动员向俱乐部医生咨询确认产品安全性(CAS 2016/A/4676)、被污染产品由队医公开发给运动员(CAS 2018/A/5853,CAS 2015/A/4129),都被认为是有利于降低过错程度的积极因素。反之,未向专业技术人员/机构咨询(CAS 2014/A/3685)或盲从非专业技术人员的推荐(CAS 2021/ADD/31),则被认为是加重过错程度的消极因素。
3)对使用产品做记录和登记。运动员对其使用的产品做记录、在检查记录单上进行登记(CAS 2016/A/4676)或准备动物食品清单(CAS 2019/A/6443&6593),均是积极履行反义务的良好习惯。其中,登记案涉产品在“非故意”认定环节被视为一种排除作弊心态的证据。在这里,该事实被用来评估运动员积极履行注意义务的程度,侧重点不一样,并非重复性评价。但应注意的是,运动员只用笼统术语列出其声称使用的产品类型是不够的,准确指出相应产品才能被认定为积极履行反义务(CAS 2015/A/4129)。
4)被污染中介体本身无可疑之处。产品污染型和肉类污染型案件中的污染中介体是物,而密切接触型案件中的污染中介体还可能是人。产品污染型案件中,被污染产品来源正规、没有关于提升运动能力的宣传(CAS 2014/A/3685)等均是表明其值得信任的原因。在肉类污染型案件中,运动员证明“肉类在当地监督管理体系下几乎不可能被污染”能减轻其注意义务(CAS 2019/A/6443 &6593)。在密切接触型案件中,长期共同居住的亲人或爱人不应被怀疑,这恐怕也是罗伯茨案(CAS 2017/A/5296)中,CAS强调来源是“运动员已交往3年的女友”这一细节的原因。反之,产品组成有异常(CAS 2016/A/4676)、非正规市售商品(CAS 2014/A/3798)或被描述为可提高身体机能(CAS 2014/A/3685)等都是体现产品可疑的因素。事实上,只要是服用营养品,就被认为是高风险的。WADA等机构对谨慎服用营养品进行了充分的风险提示(CAS 2013/A/3435),甚至发布须强制阅读的声明来确保宣传范围(CAS 2014/A/3572),对运动员注意义务提出了更加高的要求,这也是产品污染型案件无一获得禁赛期免除的原因。
5)污染发生于已知和安全的环境。在已知和安全环境下,运动员有权放松和休息,要求其每天对自己信任和熟悉的环境进行全方位的检查,是不现实也不合理的。运动员没有义务每天询问家人/伴侣的医疗状况(CAS 2017/A/5296),或在家庭聚会时询问是否有人使用禁用物质(CAS 2019/A/6482)。一般来说,运动员所处环境越熟悉、越私密,其注意义务也就越低。反之,在酒店喝茶时未亲自泡茶或至少监督泡茶(CAS 2018/A/5546&5571)等情形则被视为运动员未尽注意义务的表现。
根据西利科案(CAS 2013/A/3327&3335)确定的标准,评估过错程度须考虑的主观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运动员年龄小或缺乏经验。一般认为,运动员年龄小、经验不足(CAS 2018/A/5583)是减轻其过错程度的主观因素。尽管有案例指出,若认定运动员“非故意”时已考虑年龄问题,在评估过错程度时就不能再予以考虑(CAS 2018/A/5580)。本文认为,低龄运动员在寻求禁赛期减免时,仍应主张这一点,尽可能提出能降低其过错程度的依据。反之,运动员年长、处于领导地位(CAS 2015/A/4127)、为高水平职业运动员或具有国际赛事经验(CAS 2016/A/4676),意味着更严格的注意义务,无法基于这一主观因素获得减免。
2)运动员遇到语言或环境问题。CAS认为,运动员不会读写英语使其处于不利地位,可能没办法检查产品标签内容(CAS 2021/ADD/31)。然而,随只能设备和翻译软件的普及,语言障碍问题已很难具有说服力,但不排除未来出现新型的环境问题,会降低运动员的注意义务。
3)运动员可以合理接受的反教育程度不高。缺乏反教育(CAS 2018/A/5583)甚至从未受过专门的反教育(CAS 2021/ADD/31)均是降低运动员注意义务的主观因素。反之,运动员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CAS 2014/A/3798)和反知识(CAS 2014/A/3685)则会提高运动员的注意义务。CAS还指出,运动员在接受一些反教育后,应相应地提高风险意识,若继续实施此前的风险行为(CAS 2018/A/5583),则会被认为过错程度加重。
4)其他导致风险意识下降的个人情况。这类情况包括:承受高度压力、此前使用或检查有关产品而未出问题、因能够理解的粗心导致后续风险意识下降等。如艾拉尼案(CAS 2017/A/5301&5302)中,运动员知道母亲是一名药剂师,而母亲也知道女儿有严格的反义务。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员可以确信母亲会尽一切努力保护自身免受禁用物质污染。类似的,若运动员多年服用某产品均未出现不良后果,显然不能期望其按时进行检查每批产品(CAS 2015/A/4129)。反之,如果运动员知道某产品原版本含禁用物质,则应采取更多预防措施,以确保新配方的安全(CAS 2014/A/3572),否则就会加重其过错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运动员进入仲裁程序后的认错态度也会直接影响禁赛期。在CAS 2014/A/3685案中,CAS以“运动员要求被处以不少于 3 个月的禁赛,因其想到自己未尽力规避违规”作为评估过错程度的依据之一,最终裁定6个月禁赛期。这与我国刑法中的认罪认罚机制不同。在仲裁过程中表明认错态度并不会被视为禁赛期减免因素,反而会因运动员“也想到自己未尽最大努力”而无法减轻过错程度,更难争取进一步的禁赛期减免。此外,辅助人员的过错也应纳入运动员的过错程度评价,因为运动员有义务对其随行人员的行为负责,包括其教练员、医务人员、一同生活的亲属等(CAS 2017/A/5301&5302)。
WADC中没有关于人格证据的明文规定,但大量样本裁决书都对运动员的人格和举止加以论述,用以评价其主观心态或过错程度。在劳森案(CAS 2019/A/6313)的裁决书中,CAS甚至在结构上将人格证据与来源、“非故意”并列,在未讨论其他过错程度影响因素的情况下,直接得出NFN的结论。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这似乎表明,人格证据才是运动员过错程度的决定性因素。尽管裁决书反复强调“人格证据不是决定性的”,但这种声明显得苍白无力。
在所有支持运动员禁赛期减免请求的14个样本中,5例以人格证据作为认定“无故意”的依据;1例以其作为认定NFN的依据;1例同时以其作为认定“无故意”和NFN的依据。本文认为,从一贯清白勤勉的主观状态推导运动员无主观恶意(非故意)是合理的;反之,因一个人清白勤勉,就认定他在同等客观条件下比他人注意义务更低,是不合理的。因此,人格证据并非完全无用,但不是决定性的,只能用来认定“非故意”而不是NFN,也不应反复使用于多个环节。运动员的举止,尤其是违规后的举止,不宜用来评价运动员违规本身的过错,它可作为一种实体因素之外的评价对象,类似于刑法中的“立功”。
在WADC(2021年版)体系下,本文归纳出污染摄入型违规案件的禁赛期减免模型,并通过应用该模型回过头分析样本案例,检验模型的有效性。
在污染摄入型违规的禁赛期减免问题上,WADC总体的制度设计是以判断禁用物质类型为起点,以认定运动员是否“非故意”摄入禁用物质为前提,确定一个基础禁赛期(basic ineligibility period),并规定禁赛期减免的特定情形,以过错程度作为缩减禁赛期的标准,综合考量得出最终禁赛期。各版WADC中不同禁用物质类型下“非故意”对基础禁赛期的影响详见表4。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WADC(2015年版)和WADC(2021年版)对“故意”的释义相同,但前者指出“故意”一词是指作弊行为,后者删除了该表述,表明“故意”的主观心态不只有作弊这种动机。此外,WADC(2021年版)开始对滥用物质作出特别规定,其基础禁赛期明显低于其他禁用物质,与它比较小的危害性相适应。
除涉及滥用物质的情形外,现行WADC体系下,污染摄入型违规案件在“非故意”认定基础上的禁赛期均为24个月。表5以这一基础禁赛期为起点,对比了不同版本WADC中关于依过错程度减免禁赛期的规定。
综上,结合对样本裁决书禁赛期认定逻辑的梳理,可归纳出污染摄入型违规案件主要的禁赛期认定逻辑流程图(图2)。
在没有其他加重因素的前提下,一旦涉非特定物质案件中的运动员无法证明“非故意”,或涉特定物质案件中的反机构能证明运动员故意,运动员将面临48个月的顶格禁赛期。除涉滥用物质的案件外,“非故意”认定是运动员寻求48个月以下禁赛期的关键一环。依据样本中CAS认定运动员“非故意”的情况,形成该考量因素的检视对照清单(表6)。运动员可对照此表,检查影响自身“非故意”认定的因素,搜集相关证据。
在证明“非故意”的前提下,若运动员欲寻求24个月以下的禁赛期甚至免除禁赛,需要尽可能地列举减轻其过错程度的因素。依据样本中CAS对运动员过错程度的评估情况,形成该考量因素的检视对照清单(表7)。运动员可对照此表,检查影响自身过错程度评估的因素,搜集相关证据。
因WADC(2015年版)生效前的制度不区分是否“非故意”,故使用上述模型对WADC(2015年版)生效后的61个样本案例进行检视,发现大多数裁决书的论证过程都符合图2的逻辑流程,除双方当事人对部分事实无争议的情况外,一般都按照先讨论来源、“非故意”,再讨论过错程度的逻辑展开。上述样本中,不全部符合这种论证结构的有5例,对照模型,对其中的4份裁决书做多元化的分析,CAS 2017/A/4954中补充讨论过错程度的做法对裁决结果无实质影响,也未减损运动员权利,故不予详细分析。
该案裁决书在论证来源后直接得出结论,认为“这种污染途径是运动员永远想不到的,所以他没有过错或疏忽”,并免除其禁赛期。本文认为,本案中的证人证言颇具疑点,运动员的女友称自己连继父的职业(导演)都不知道,却信任他并服用其购买的来源不明的药物。即使证明了来源和“非故意”,只要考量运动员的过错程度,就会发现他至少在3个方面未尽注意义务:一是,他已和女友交往3年,鼻窦炎作为慢性病是日常生活中易被观察、了解到的,他理应知晓女友的病情和她服药的事实;二是,接吻导致违规并非没有先例,早在加斯奎特案(CAS 2009/A/1926&1930)中,就存在运动员与陌生人接吻导致违规的情况,更何况本案中运动员与女友长时间亲吻,只会比加斯奎特案的风险更高;三是,即便接吻这种污染途径如裁决书所述,是“永远想不到”的,运动员还和女友共用一个水瓶饮水,且未作任何询问和预防的方法,显然未尽到一名职业运动员理应承担的注意义务。
该案裁决书先对来源和“非故意”进行讨论,然后对运动员的品格证据进行了大段论述,在未讨论过错程度的情况下,直接得出NFN和取消禁赛期的结论。这种草率的论述也是本案被许多学者诟病的原因之一。前WADA合规审查委员会主席Taylor(2020)认为,本案裁决观点形成了“糟糕的先例”。如果对运动员的过错程度进行详细讨论就会发现:在客观因素方面,作为一名理性的运动员,外出就餐(尤其是食用肉类制品)时必须小心谨慎,若食用受污染肉制品未能短时间内代谢,有几率会使阳性检测结果,运动员显然未尽严格注意义务,也没有满足合理期待;在主观因素方面,当事人作为一名职业运动员,根据其自身条件与能力,不存在任何阻却过错成立的证据。
该案裁决书的逻辑结构完整性有所缺失,在认定运动员无法证明来源的基础上,直接忽略了他基于特殊案情仍可证明“非故意”的可能性,作出禁赛48个月的裁定。尽管概率很小,若运动员能通过“最狭窄通道”,其禁赛期可基于“非故意”降至24个月。鉴于本案案情没有突出的特殊性,运动员显然不可能通过“最狭窄通道”,裁决结果在实质上是公平的。但忽视运动员有机会获得禁赛期减免的救济路径有违程序正义,可能会引起实体上的不公平,既不能够确保类案裁定的一致性,也不能起到充分警示、教育其他运动员的作用。
该案裁决书采取一种所谓的“系统化”论证方式,通过列举一系列有利于运动员的证据,指出“他是危地马拉肉类污染的受害者”,并在没有详细讨论“非故意”和过错程度的情况下,得出如下结论:“动员在检查前1天食用的肉类很可能受到禁用物质污染,这是非故意的。在确定运动员对违规没有过错或疏忽后,根据UWW ADR第10.5条,取消原本适用的禁赛期,不予禁赛。”本案在过错程度的客观和主观方面,与劳森案类似,同样不宜得出NFN的结论。裁决强调“危地马拉在畜牧养殖业中使用生长促进剂的情况普遍为人知晓”,这固然有利于运动员证明来源,但无疑会促进提高他在该国食用肉类时的注意义务。CAS避开上述讨论,直接得出NFN的结论,显然是不合适的,比劳森案的不当程度还要高。
由此可见,运用本文提出的禁赛期减免模型起草裁决书更具说服力。省略部分关键论证环节的上述4份裁决书无疑是草率的,令人怀疑仲裁员其实就是无话可说、无理可述,极大影响了CAS的公信力。
对CAS而言,本模型可用于检视裁决结果的正确性,保证裁决书说理的逻辑完整性,避免裁决观点依据不足、恣意省略关键论述等情况;而反机构可以反向利用本模型对污染摄入型违规案件做评估,提出不利于运动员禁赛期减免的证据,从而争取胜诉。本模型以运动员权利保障为研究起点,对运动员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作用:
在未发生污染摄入型违规案件时,运动员通过学习本模型中的逻辑流程图和检视表,可以充分认识此类案件中存在的违规风险及其难以处理的后果,系统、清晰地了解此类案件中禁赛期的认定机制。同时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反义务,以及履行该义务在主观层面和客观层面上的具体实际的要求。运动员可直观了解到,为避免发生污染摄入型违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细节是应该做到的。
当运动员身涉污染案件时可以依据本模型预判禁赛期,对照相关正面及负面清单搜集证据,尽可能争取最大限度的禁赛期减免,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虽然人格证据并非决定性因素,但运动员在违规发生前的清白记录、对待反义务及反教育的良好态度,违规发生后的配合举止、努力调查来源的积极举动等,都可能被CAS认定为禁赛期减免因素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